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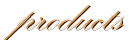 你的位置:500快三彩票官网平台 > 新闻动态 > 明朝崇祯年保定织妇张刘氏的辛未年
你的位置:500快三彩票官网平台 > 新闻动态 > 明朝崇祯年保定织妇张刘氏的辛未年崇祯四年(1631年),霜降后的第七日,保定府清苑县西巷的石板路上结着薄霜。张刘氏掀开土炕上的粗布被子,脚刚沾到青砖地便打了个寒颤——自去年开春丈夫张二顺跟着商队去了张家口,这土炕便只剩她和五岁的儿子虎娃,还有西间屋咳嗽不止的公婆。
灶膛里的槐木噼啪作响,刘氏往锅里添了半勺稗子面,搅出稀汤寡水的面糊。虎娃攥着半块硬窝头啃得咯嘣响,她摸了摸孩子冻红的小脸,转身掀开北墙根的草席——六架纺车并排靠墙,最左边那架还是成亲时阿爹亲手打的,车轴上的红漆早被磨得发亮。
“今日得纺完三斤棉条。”她对着空气念叨,指尖捏住棉桃里的白絮。去岁县里推行“改折”,原本缴粮的赋税折成白银,每亩地多摊了二十文,逼着家家户户把织好的布往当铺送。刘氏低头看看自己手腕上的旧银镯——那是嫁过来时的唯一首饰,上个月刚典给了南街的王掌柜,换了三斗粟米。
西巷突然传来狗吠,刘氏心里一紧。果然,巷口传来里正的公鸭嗓:“各家各户听着!今冬加派'辽饷’,每户织妇须多缴二匹细布,三日内送到县署!”炕上的公公剧烈咳嗽起来,婆婆颤巍巍摸出个陶罐:“剩下的棉花……怕是不够了。”
刘氏捏着梭子的手发颤。上个月她刚把新收的棉花卖了一半,换钱给公公抓药。此刻竹筐里的棉桃只剩小半筐,棉籽上的短绒都被刮得干干净净——那是她连夜用铁梳子梳下来的,本想留着给虎娃做双新棉鞋。
“阿娘,疼。”虎娃举着被棉刺扎破的手指哭起来。刘氏扯下衣襟上的碎布裹住孩子的手,突然想起三年前,丈夫走街串巷卖布时说过的话:“北边的鞑子又抢了大同,官府哪会管咱们织妇的梭子有没有断?”
晌午喝了碗菜糊糊,刘氏挎着竹筐往城隍庙集市赶。筐底垫着半匹未完工的青布,边角处还留着没挑干净的棉结。她在布摊前转了三圈,终于咬咬牙:“王娘子,用这匹布换两斤棉花,行不?”
卖布的王娘子扫了眼布面:“粗布换棉花?你这布上的经纬都歪了,顶多换一斤半。”刘氏的脸涨得通红:“我昨夜熬了三更……”话没说完,街角突然传来喧哗——几个衙役拖着个老汉往县衙走,老汉怀里的棉包散了一地:“冤枉啊!小老儿实在凑不出辽饷!”
刘氏猛地转身,把青布往王娘子手里一塞:“就一斤半,给我吧。”她抓过棉花往筐里一埋,仿佛怕被人抢走似的,脚步匆匆往家赶。路过豆腐摊时,虎娃扒着摊子咽口水,她摸了摸袖兜,那里躺着卖旧铜盆换的五文钱——这是给公婆抓药的钱,半文也动不得。
掌灯时分,刘氏在炕桌上摆开瓦罐:黄豆二十粒,粟米半升,盐粒可数。虎娃早已饿得趴在纺车上睡着,她轻轻给孩子盖好补丁摞补丁的被子,又往灯盏里添了半勺菜籽油——这盏灯要支撑她织到子时。
机杼声在狭小的土屋里回荡,刘氏数着梭子来回的次数:“一梭,两梭……十梭一丈,百梭一匹。”突然,西间屋传来“咣当”一声,她慌忙跑过去,见婆婆摔倒在地上,装棉籽的陶盆碎了一地。老人哆哆嗦嗦往起爬:“想着把棉籽磨碎了熬汤……给虎娃补补。”
刘氏鼻子一酸,搀起婆婆时,摸到老人瘦骨嶙峋的手腕——和她握梭子的手一样,布满了被棉刺扎出的血点。墙角的米缸空得能照见人影,她突然想起去年秋天,丈夫托商队捎回的半块砖茶,还藏在炕席底下。明天,或许该拿去当铺换点小米了。
更夫敲过三更,刘氏的眼皮重得像坠了铅。织机上的布帛刚织到三尺,梭子却突然断了——那是用了十年的枣木梭,裂纹里还卡着没剔净的棉线。她摸黑找到备用的柳木梭,突然听见远处传来狗吠,还有马蹄踏在青石板上的“嘚嘚”声。
“莫不是鞑子又打过来了?”婆婆在黑暗里喃喃。刘氏心口一紧,去年冬天,涿州传来消息,说清兵破了城,城里的织妇连织机都被抢去当柴烧。她下意识把虎娃往怀里搂了搂,指尖触到孩子后背的补丁——那是用她成亲时的红盖头改的,如今红布早已褪成粉色,补丁上还绣着半朵没完工的并蒂莲。
梭子在经纬间穿梭,刘氏盯着布面上歪歪扭扭的纹路,突然想起十六岁那年,在娘家的小院里学织布,阿爹说:“女娃娃的手巧,织得好布,就能寻个好婆家。”如今她的手早已磨出老茧,布却越织越粗——不是手笨了,是棉絮里掺的草梗越来越多,梭子在草梗间卡得生疼。
当第一声鸡鸣穿透晨雾时,刘氏终于趴在织机上睡了过去。梦里,丈夫背着布包推开柴门,笑着说张家口的布卖了好价钱,给虎娃带了块芝麻糖。她伸手去接,却看见丈夫的布包里露出半截断梭,染着暗红的血……
“哐当!”院门被风吹开,刘氏猛地惊醒,只见窗纸上泛着青白的天光。她揉了揉发麻的手腕,摸过枕边的梭子——新的一天,又要在机杼声中开始了。而墙角那匹未完工的布,将在三日后被官差收走,换作账本上的几个墨字,或是远处战场上的一声炮响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Powered by 500快三彩票官网平台 @2013-2022 RSS地图 HTML地图